
▲ 济州的茅草屋 摄影:Cat Lever
一、
造物主的灵性和魅力在于,用不经意的作为造化出让人类感激零涕的东西,那实在是一些人类穷尽毕生精力也模仿和制造不出的景象。
生动流转的九寨沟,终年积雪覆顶的富士山,温情萦怀的多瑙河,还有我脚步刚刚踏入的济州岛,它们应当属于这样的景象。
济州,韩国的一个小岛。
70万年前,北太平洋的海底催生出这样一粒别致的岛屿。
似造物主随心所欲地别在海洋怒涛上的一枚徽章。
那时候,即使有意识的生物怎么会想象得到今天我们过往的脚步和不尽的慨叹呢?
70万年,对万古的宇宙而言,可谓一瞬。70万年,对短暂的生物而言,可谓遥远。
只是,我触目的色泽,大约在不息的台风和海浪的揉搓拍打中,依然经久顽愚地用清晰的磨砺痕迹,诉说着70万年的经历际遇。我吐故纳新的气息,想必也会经久不息地以湿润清香的纤纤秀指,撩动诧异不堪的远道而来的任何心意。
济州,长在海中的一枚礁色莲座,漂在海中的一片褐色枫叶,伫立海中的一位绝代佳人。
二、
要解释物质和地质的生长过程,我的贫乏显而易见。
只是在时间的某一个刻度上——70万年前的某一天,一个岛屿,涅磐于海底。即使拥有神助的想象,我所能思想和揣摩到的这个岛屿也不过是一个擎天的石柱。或者一座浮出水面的石山。或者一尊筋骨凸出的巨型雕像。
像颧骨高耸的北京猿人,像青筋暴跳的农夫,还像错落有致的美女,就毫不暧昧地凸出着,分明了自然的法则,说明着物质的成长。
而到底凭着怎样的力量,北太平洋上就成长了这个海岛?
经验的解释,是海底的一次燃烧。用激烈翻滚、猛烈喷涌的方式。而后,熔化翻喷的岩流就以岛屿的形态把不灭的物质矗立于太平洋之上。
柱状岩,三枚峰,虎岛,蚊岛,万丈窟。它们,不经意地美丽了这个海岛,仿佛戈壁,胡杨或者戈壁之上的雪山。
造物主的意志有时候强大得有些诡异。
三、
终于,复归为思想者一样的沉静。是黑色的思想者。
黑色,燃烧的结果。浓缩了时间焰火的一个过程,却不灭地留了下来。执著地诉说着物质运动强硬得有些缓慢的哲学命题。
颜色,却注释着生长的过程。海岛济州,我容易地产生了这样一个判断。
我的脚下,一个唯美的黑色佳人,会暗示些什么给我的想象?
在节气的战栗和推拥中,石岛滋润出的内敛着阳光之色的一枚果核,蓬勃着嫩绿的,柔软的,滑润的果肉,濡染些许茸茸天然的鹅黄色,再点缀些丰盈成熟的赤橙色。如一枚让人口津生香的水蜜桃,就有禁不住吞吐的欲望。
一位盈盈流香、出水芙蓉般的女子,一帘绸缎般温柔浪漫的轻纱,通透流连的眉眼里跃动着,月光般质朴的醇美色气,在四季海风的拍抚鼓励中,成熟的各种色泽,次第地流动开来,恰如变换出了得体而不狐媚的衣饰。
济州,好一位靓丽的韩式美女,暗香浮动的肌体上,还要吐纳出一袭素缟般的天地渊,还要独立着雄性卓然的汉拿山。
而黑底色的石岛,智慧地把各种色彩的情意和味道,放在时间和季节的秋千上,在日月阴冷不定的眉眼下包容于怀,送高送远。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情形:黑石头的地基,黑石头的房础,黑石头的墙壁,黑石头的田垄。时序,把它们码得整整齐齐,像一种秩序。
永远冷静寂然的色泽,永远辽阔沉实的舞台。季节,最有才情的艺术家,不知疲倦地导演着。于是,激情的粉红色,高贵的金黄色,热烈的大红色总是在浩渺烟波的张驰律动中,轻曼地登场舞蹈。
只是极少有轻浮的脚步,海盗的,海女的,乌鸦的,动物的和我们的脚步,打破70万年的沉静。极少有炊烟,掠夺和不怀好意的炊烟,改写水天的感受。
四、
大唐帝国生长扎根在厚厚的黄土里。我轻薄地行走在厚厚的黄土之上。很久的一段时间里,我与石头的关系简单而明了。母亲青色捶布石头和我家头们的青色门墩,凉爽过我近二十年的记忆。
走出泥土馨香的乡路后,我所见到的石头不过是掩盖了盛唐气势的一脉浅山。
石头,保守着历史的秘密。
在艺术的大唐石头里,我揣摩过一个帝国的气度和表情。六十一个宾王,列队的文武官员,夸张的狮兽,向天的华表,沉淀着时间的骨气和精髓。
石头,诉说着历史的风度。
济州生长扎根在神秘的太平洋海底。而千姿百态的嶙峋怪石,虎啸深林、马驰疆野、游龙卧波、鹰击长空的样子。
蜂窝洞孔一样的石头,遍岛都是。蜂洞,密集而又充满玄机。造物主的专注,令人肃然起敬。一想到岩溶管喷的烈度,我就浑身开始燥热。
可想象空间的窄狭显而易见,我最为容易的比喻不过是像沙锅翻滚着疗疾的中药草。母亲蒸煮包谷的滚锅。乡下老奶奶发酵的醋缸。北太平洋喷发的气泡。
我还想到盛夏时间,急促的一阵暴雨打湿浮尘的乡路。想到绵密的细雨拍击湛蓝的荷田。
它们都坚持着一种无为而又智慧的流程。
遍地的石头。聚会的石头,盛宴的石头,激流的石头。
大唐帝国、济州海岛,谁雕饰的石头?修饰谁的石头?多么遥远的石头?
过往的时间和时间的主人都清楚。
五、
佛祖的力量有多久远?
打我记事起,我母亲每晚都要手脸洁净地给菩萨磕头敬香。在她的信仰里,慈祥和善的菩萨善良仁厚,具有保佑平安、驱除邪恶的力量。我也拜见过乐山大佛,拜见过彬州大佛,我还拜见过几十处的观音佛祖。
我母亲的膜拜,我的膜拜和海岛济州的膜拜都具有精神诉求的动机。我们都拜见着一尊雕像。
黑色的石老人,被世代的济州岛人尊为神圣之物,站立在海岛的任何一处默默守望。长者敦厚、仁慈的模样。想发财,拜之。想升官,拜之。想生儿育女,还要拜之。就在抗议进口美国牛肉的首尔游行队伍中,有青春的学生们也举起了石老人的画像。信仰的坚韧其实不比石头柔软多少。
一定是我们公祭着的生金的土地爷,助福的财神爷,佑护的菩萨了。而要计量它的多少还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情。可是,随时的每一次相遇总要自然地给人增添几分敬仰。文化相互通融和体恤的功效油然而生。
黑色的石美人鱼,独立于一处叫做龙头崖的海岸边,眉眼逼真得有些忧郁。用目光体贴她的心思,疑心它实在是要把女人的盼望倾诉给浪涛连天的大海:美人鱼——大海的女儿,为什么仍要作为海女?
黑色的龙头,桀骜不逊地伸出海面,做仰望天汉,腾云驾雾,长啸不已的样子。水浪就汹涌地滚过来,生气似地击石拍岸。恰似蛟龙的身体依然还游动在海水之中。龙头岩,物主把神奇的杰作交给海天交融的小岛。
小岛,就一直把佛祖的故事,把图腾的佛祖诉说给将来。

▲ 照片出自《由照片了解济州史》一书
六、
金黄的油菜花,橙黄的柑桔花,粉红的樱花发芽、盛开在顽愚而疲惫的石头之上。让生命的巍然和依附有了很难思议的可能。
而海风和金色的阳光用优美雅致的弧线不倦地轻抚着各种生物。时而矜持,时而轻狂。却随心地滋养出一种怡然天外的田园和贴切率真的风气,俨然世外桃源,俨然人间仙境。
竖石为墙、结草为芦,古香古色的茅庐。仰视,如一朵朵泛黄的鲜蘑。俯视,似夕阳余晖下在白浪中荡漾的浪花。遥望,像雨后在空辽牧场中悠然食草的一群黄羊。
不变的尊贵的黄色民居,见证过大长今的故事,也见识过韩剧里少男少女的青春偶像。
城邑,古色的民俗村,见证着我钦仰的心眼,无往地轻松了我世俗和功利的眼神。
我走过藏族的山寨,走过蒙族的敖包,走过绝版的周庄,也走过小日本的白川乡,而济州先民的寓所就从触目的那一刻起,牢固地铆在心底。
七、
由海拔近千米的关中走到隔着太平洋的海平面上,我用了40年的时间。我不可能走到地球海拔的最高点,我却可能走到海拔的零点。我还畅想过海拔最高处的风光,我却没有想象过海平面的气象。
海拔1980米是高山?海拔180米也算山?是的,济州妩媚地向世界说:那是汉拿山,那是城山。
山顶上是一片近千平方米的盆地,想见久远以前管喷的气势,该是怎样的巍然壮观。这也是山峰?济州喜气地给我们说:那叫城山日出峰。
而我,几乎是站在海平面上张望孤立的城山,四野水天一色,朗朗开阔。疑心城山是一个独立水中的君王,把黑色的桂冠浮出水面。
行走在城山的开阔的斜坡上,心底轻易地浮起一缕得意。就把身子躺在绿茸茸的草地上仰望。任海风怂恿的海浪声翻乱头发和心思。忘我,随意的形式。
而窜入心底的缕缕清香,一直提示着我对土地的远离和背叛。
鲜嫩的青草铺满了一洼山巅,是一片牧场。思维早就像一群急不可耐的绵羊。
轻妄地踏过君王的头顶,谁有这样的胆量和福气?谁可承受这样的轻狂和虚无?
山顶眺望,海面无疆。一波一波汹涌的海浪,推拥着轻柔的海风,淘洗的是浮尘的心思和面颊。
八、
驴,最为苗条的牲口,和马、牛一起耕种过土地和我们的记忆。
不光凭着牲口的粪便就可区分它们谁是谁,甚至凭着它们大粪的气味,我就能分辨出牛粪、马粪和驴粪。可耻的是,二十年前至今,我再也没有见过驴了。
怀念驴,已经是不少人的一种情感活动方式。而我,对驴的最近一次回忆,是在丁亥年的冬季。
狂妄的飞雪激起我对乡下父母的无尽牵挂之后,卑劣地阻断了我的乡路。我曾经说过:某夜,一个村姑牵着一头叫驴踏破我的梦境。为什么是这样的梦境?还周折过我。
现在,一阵海风送来了盆栽艺园里的花草馨香。深深地呼吸。呀,有驴粪的草味!我有了些惊异。
在礁石盆栽的艺园里,我四处张望。果然有驴,是线条流畅的驴!七八头圈在隔壁栏栅中的济州驴。
小戴和小沈,两个生活在古长安的清丽女子,端庄大方,典型的东方美女。高楼林立的长安都市肯定在不久以前的很长时间里,拥挤着她们的神经。想必她们从一出生就没有见过毛驴,清澈的眼神里有掩饰不住惊喜,欢呼致意着不期而遇的毛驴。
我,会意地笑。欣赏地笑。揶揄地笑。
也巧,就有一头步态悠然地过来了,用匀称的鼻息和一鞭光滑摆动的尾巴呼应着美女的呼叫。俨然相遇分别经年的故友,目光透着水一样的亮色。
隔着木栏,濡染唐风的小沈折枝逗弄,用毛辫女孩式的天真挑战着驴友的耐心。不温不火,驴,用绵长的耐心和伶牙俐齿轻逐绿枝。
她们在丛林掩映的石林前形成了阔别已久的美丽关系。
嬉笑。不再骄矜的中国美女,喜气萦怀。好开心的纯朴女子。
细嚼慢咽。还旁若无人、随心所欲地晃动着长耳和后股之间的器官。好优雅纯洁,真实无邪的驴。
海风轻曼地飘动,似乎入心的清流或者舒坦的乐曲,人贴心得筋骨松软。
我想:这样一个浪漫的海岛,馨香的海岛,一定是要盛产美女和驴的。
果然,三天后在首尔的国际会展中心,济州向世界人民展示的是一头光滑洁净的毛驴,毛驴的身边站着一位身材高挑的韩式美女(我还为美女和驴的完美组合拍了一张照片)。
九、
我毫无准备地想到了一个词语:地老天荒。长久也地老天荒。一瞬也是地老天荒。大规模的造词运动给我留下了这样一个激烈冲突的感受。
想到这个词语的时候,我的情绪正为一种景象所激动。
润洁的海风舞动金色的艳阳,轻柔的涟漪推拥绵密的白沙,偶然划过海滨水面的目光,惊飞原本矜持的海鸟。
潮汐过处的浅滩,微风摇曳着婷婷韩女的身影。
从容。大气。贵美。秀发翻动。衣袂翩然。眉眼和煦。
该是惬意的美景。该是浪漫的风景。该是甜蜜的所在。
一对在日本蹄铁下惊恐结婚的韩国老夫妻,告诉自己的女儿:去济州渡你的蜜月。老夫妻的神情让初为新娘的女儿不解。女儿,把父母的愿望和潇洒的新郎一起携拥到济州。
一对小夫妻在秀美温馨、不染俗尘的济州开始了人生的喜剧。
浪漫。刻骨铭心。唯美的一程。
洁净的海水浇灌着爱情。温柔的海风滋养爱情。小夫妻,你们比父母拥有的更多。
一个月后,老夫妻见到了喜气的儿女,哽咽地说:我们完成了最后一个夙愿。
我有些感动于这个故事,为老夫妻的心意。
还是海风,把夜晚昏鸦一样摇落在地。我孤寂地散步于海边。天海深处漂浮着几枚闪光的星辰。
就想:几十年以后的小夫妻,会给自己的女儿说些什么。
海岛济州,你当然知道。
作者简介
庞联昌,中国散文学会会员,陕西作协会员。曾在《十月》《美文》《青年文学》《散文》《散文选刊》《延河》《青海湖》《小品文选刊》《手稿》等刊物和《人民日报》《陕西日报》《西安日报》《华商报》等省级以上报纸副刊上发表过文章。长篇散文《盗墓的历史》2009年在《美文》专栏连载出。
出版《庞联昌散文》和《皇陵破》等文集。
庞联昌 contributor@jejuchina.net
<© 济州周刊(http://www.jejuchina.net), 未经许可不得擅自复制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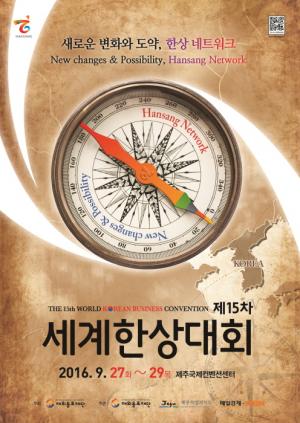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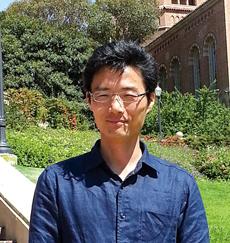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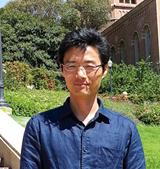





 风变成了光,照亮夜晚的济州大海
风变成了光,照亮夜晚的济州大海

